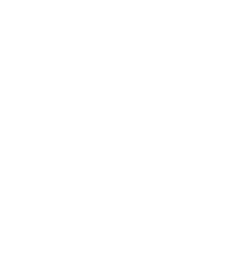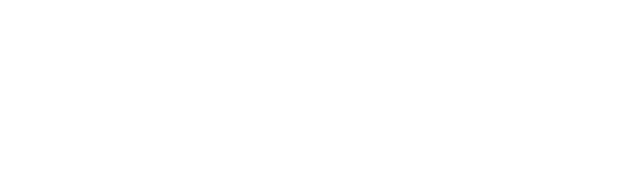7月13日中午,当我穿过花园里的喷水池时,突然接到湖北作家陈敬黎的电话和短信息:“陈老师,汀泗桥在恢复历史古迹,汀泗桥镇的有关领导读了昨天《光明日报》上的评论文章《当代才子陈奕纯》后,经过认真考虑,决定请您题写‘汀泗桥’名,我很希望把您的墨宝永远留在这座历史名镇,永远留在我的家乡。”
我顿觉自己像池边那一排木棉树一样挺拔,像池边那一排榕树的气根一样清爽。

汀泗桥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,北伐战争使它名扬天下。历史选择了汀泗桥,自然有选择它的理由。
汀泗桥建于南宋淳祐七年,是当地一个名叫丁四的农民打草鞋卖,集资修起的一座有楼有台、可为行人遮风雨的石拱廊桥。后人记其功德,取此桥名为丁四桥。此地繁荣得益于沟通长江大水道的一河清水,故从水改名为汀泗桥。地也以桥名,至今八百年。
盛世修楼台,是历史彰显德政的记忆。世上几多楼台兴于治,废于乱,成了朝代更迭的见证。治则兴,乱则废,是楼台命运的不二选择。汀泗桥有幸,这座废于北伐战火的廊桥,今日适逢太平盛世,重修了,又红梁碧瓦地再现人世,乃汀泗桥大幸!乃国人大幸!桥兴人旺,桥废人亡。匠工修桥的锤声,仿佛枪声、马蹄声,又在这座千年古镇响起,惊动了在汀泗河上静静躺了一个甲子的汀泗桥。汀泗桥用金戈铁马之印痕,把历史记忆刻在桥墩上。那上面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戈印;有辛亥革命志士的足迹;有北伐将士攻打汀泗桥的弹痕;有日本鬼子的铁蹄迹,有谋求民族独立的仁人志士的血印。改变中国近代历史走向的每一次惊涛骇浪,都汹涌地拍打过这座南鄂小桥。

汀泗桥是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区出长江水道的必经之地。因其北、西、南三面环水,扼粤汉铁路之咽喉,据守近在咫尺、几度成为中国京畿重镇的武汉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是南粤经长沙过岳阳到武汉的关隘。得汀泗桥,则武汉安,失汀泗桥,则武汉危。因此,汀泗桥成为兵家为得九省通衢武汉而决一雌雄的必然战场。
2008年春天,我应邀为中南海创作了草书八条屏毛泽东《沁园春•雪》、八条屏苏轼《水调歌头》;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了草书对联《渊深鱼乐,树古禽来》、八条屏毛泽东《沁园春•雪》、以篆隶入草的六条屏毛泽东《沁园春•雪》,还有草书中堂陶渊明《饮酒其五·结庐在人境》、李白《望天门山》等等,其中我比较满意的是草书六条屏杜甫《秋兴八首其一》、中堂李白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,其构思立意、谋篇布局,惨淡经营,有陈氏的创新意识。2011年冬天,我应邀为中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题写“感恩亭”时,我想这三个大字的风格应该在雍容宽博的气度中增加些凝重,不能随手一挥,于是在以往的帖写中揉进北碑的特点,反复书写,一个月后顺利交稿。如今,要题写的“汀泗桥”,它不是一个普通的、简单的牌匾,它承载着中华民族一段非常特殊、复杂、厚重的历史,不是任何一种书体都能担当得起。所以,我下决心要打破自己以往固有的书法模式,力图笔墨情趣随题材、内容而变化。可是,每一种书风的形成是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,短时间内要改变、突破谈何容易?我只有紧紧抓住书法创作的三要素——形式基点、技术品位、创作意识。
7月16日,白天我浸泡在前人的碑帖墨迹中,夜里连续书写了五个多小时,一无所成。当天友人陈敬黎发来三条短信息来催稿,一再强调要写成擘窠大字,原作要给北伐汀泗桥战役纪念馆收藏、悬挂,我有些着急了。
7月17日,白天我又浸泡在前人的碑帖墨迹中。晚饭时,有一位爱好书画的朋友来电说要过来品茶聊天,被我婉辞了,问及原因,我说要题写个桥名,他说现在是商品时代追求效益,大多名家驾轻就熟写几个小字给人拿去放大就行了,没人讲究有无山林气,何必费那么多精力?我淡然一笑,不置可否。当夜我尝试用茅龙、狼毫、兼毫、羊毫各种笔书写,捣腾了一夜,效果不佳。
7月18日,我关闭所有通讯工具,日夜临习摩崖刻石《石门铭》、《瘗鹤铭》、《经石峪金刚经》,企图从中寻找到最佳的感觉。
7月19日,我又关闭所有通讯工具。白天我还是浸泡在前人的碑帖墨迹中,晚饭后我就开始做好创作准备,写写停停,停停写写,忽然发现在仿古宣粗涩的背面上书写效果更好,当翌日的第一道晨光射向我的画案时,渴求已久的“线的美”、“光的美”、“力的美”齐齐到来了,“汀泗桥”三个大榜书在重笔疾挫、气酣墨畅中诞生。
如今,“汀泗桥”三个大字已雕刻在两大块厚重的红褐色菠萝格木板上,描上墨绿色油漆,镶嵌在汀泗桥两端,向过往汀泗桥的每一个人讲述汀泗桥历史。陈奕纯
作者:陈奕纯
来源:咸安旅游